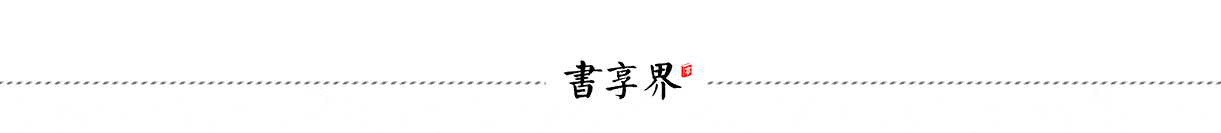

△吴春波
版权声明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chnstonewx),书享界(readsharecn),本文摘编自《在悖论中前进》
作者:田涛,华为管理顾问
历史不能假设,华为选择IBM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逻辑――一个传统经典的美国老牌科技制造企业,一个凝聚着20世纪美国经典管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流程的伟大公司,从侧翼助力,把华为带上了从传统“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转型的“不归道”,带入了全球化企业的行列。
1
江湖组织
朴素粗放的组织活力与自毁机制的滋长
1987年,一个少年时崇拜希腊大力神,崇拜李元霸、宇文成都这样的盖世英雄,崇拜“力拔山兮”的项羽,44岁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都处在人生逆境”中的前军人和落魄失意的前国企部门主管,因生活所迫,创立了一家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个体户”企业。在做技术专家的梦想破灭后转身做组织者,对任正非这样内心孤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来说,他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作“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
任正非写于2011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生动描述了创业初期华为“活力与混乱”并存的状况,也描述了作为企业家的他的身心困境: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
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
前10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
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
到19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
任正非甚至形容当时的华为是“春秋战国”。“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以上几段话,透露出几层含义:
一、充分放权是华为早期迅猛扩张和崛起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权力的充分开放与释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华为得以从“四大皆空”——无背景、无资本、无人才、无产品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一位华为前高管对我讲:“虽然那时的华为四大皆空,但老板总是在给我们讲理想、讲未来,我们也都年轻单纯,愿意相信他。他讲要吸引‘胸怀大志,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加入华为,到了华为,给你比外面多很多的钱,也给你天天讲理想,也给你自由发挥的空间,提拔得也快,当年很多干部都是坐火箭上来的,所以大家干劲也大……”
二、充分放权与释权带来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弥漫。而这和任正非的英雄主义情结密不可分,也许在创业初期,这正是他所欣赏和期待的结果。
三、创业之前的任正非几乎从未从事过管理工作,对人性的复杂性、组织管理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华为创业早期的文化与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早期并无太大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原始积累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商业文明稀缺和现代管理思想贫乏的大背景下,企业家们依赖个人本能和经验进行管理,江湖化管理是普遍现象。
四、做“甩手掌柜”是为了“遍地英雄下夕烟”,但也有可能“遍地是狼烟”。英雄主义文化的异化使得华为成为“春秋战国”,思想多元,主义林立,这显然是任正非不想看到的结果。华为如果不能构建统一的价值观、构建系统的制度与流程体系,大概率走不出原始积累期,大概率会如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一样“大碗吃肉,大口喝酒”,风风火火10多年,最终以大悲剧而收场。
因此,在《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中,任正非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帮助制定了《华为基本法》,而他在过去的20多年中更是无数次感谢IBM。《华为基本法》在华为从原始积累期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关键阶段,推动华为几千名知识型劳动者统一思想,凝聚共识。IBM则是在观念、制度、流程方面使华为迈入现代管理轨道,从对人的依赖走向制度依赖、流程依赖。
我访谈过数十位华为创业早期的老员工,那个时期,他们无不是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今人到中年,并成为华为公司高管、技术领军者、专家,他们都带着一丝神往的表情,憧憬地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当我问道:华为还能回到那个“自组织”的时代吗?有人答:“回不去了,也不能回去了,那样的华为会崩溃掉,走规范化管理的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也有人讲:“华为不能因为规范化管理,扼杀人才,扼杀个人英雄……”
2
自组织管理
一种反人性逻辑的乌托邦理念
20世纪90年代前后,硅谷涌现出了一批与美国传统企业在管理文化上迥然不同的芯片公司、网络公司、科技制造类公司,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创始人大多是技术至上主义者,大多崇尚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而企业的员工构成也主要是技术专家、软件程序员为背景的知识型劳动者,同样酷爱个人自由与平等,他们每天10多小时的“跨时区奋斗”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兴趣,有些人怀有强烈的“技术主宰世界、软件定义未来”的“上帝梦想”。这些公司的组织方式大多是高度扁平化的“自由人联合体”,而非科层制;工作方式大多是自主的与自觉的,以及鼓励试错与包容,而非任务型、命令式的。那些充满创造能力和能量的“牛人”们对企业环境中的自由负离子高度敏感,稍感不适就可能来一场绝无留恋的告别,或者被风险资本引诱而去另立山头——创业,或者加盟别的企业;他们的生活形态被称作“牛仔式的”——反叛的、自我为中心的、我行我素的,而非秩序化的、集体主义的、循规蹈矩的。
这些公司是一类组织新物种,也曾吸引了管理学者的关注,过去20多年关于互联网企业组织的研究、关于科技企业组织的研究、关于知识密集型企业组织的研究成为美国管理学界的“显学”(中国管理学界紧随美国之后),研究著作、论文、案例汗牛充栋,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也包括“新瓶装旧药”,自组织管理理论就属于这一类。
作为一种美好的乌托邦,自组织管理在东西方管理哲学中一直拥有突出地位。比如,东方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在悠久的管理实践史上也有许多美好传说,但最具代表性的则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与实践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罗伯特·欧文年轻时是英国一家纺纱厂的老板,他倾尽心力要在企业中创立社会工程学的模板:接近理想的工业环境,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社区。欧文改革实验的原则是:既有利于资本和企业家,又有利于劳动者。其核心内涵是,生产资料公共占有,人人权利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为了进一步验证他的思想主张,54岁的欧文赴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他的计划是挑选约2 000位科学家、学者、艺术家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起住在一座巨大的四方形院中,自行管理,以高效的方式共同耕作,过着无须金钱的和睦生活;人们在花园中进行社交,辛苦劳动,适度节欲。但这样的社会工程实验在进行不到两年后,公社便开始分崩离析,分裂成了10个派系,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吵架之中,每个派系都争相改写社区的生活与劳动规则,“争夺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最后,欧文的自组织实验在复杂的人性冲突中失败了、幻灭了。
欧文的自组织管理理想曾经穿越时空,影响了东西方社会,包括中国的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也包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任正非曾经告诉我:“我早期创立华为时,在管理上受到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华为实行的“员工普遍持股制”——“人人做老板,共同打天下”的股权制度的思想源头中无疑有欧文的某些影子——虽然这种模式也是生存危机逼出来的。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描述的华为创业早期10多年的管理状态,也非常类似于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自组织管理。与罗伯特·欧文不同的是,任正非在遭遇人性困境、组织困境时,选择了拥抱西方主流管理思想和制度体系,选择了向IBM这样伟大的企业和一流的美国咨询公司学习,在他早期朴素的理想主义元素中,嵌入了更现实主义的科学管理思想、制度与流程框架。而欧文却终其一生而不改,在不同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创建自组织社区,最终无一例成功。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初,硅谷的许多创业公司也无不是从自组织起步,最终要不走向解体,如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要不演进成“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复合体,比如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前总裁安迪·格鲁夫常用的管理技巧是“抓住某个人,用大锤敲他的头”,他对控制的热爱,胜过了一切。《芯片战争》(Chip War)的作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评价说,“真正拯救英特尔的关键,不是创新或专业,而是格鲁夫的偏执,他让英特尔变得不像实验室,更像一架准确调节的机器”……
这些成功与失败的企业案例不计其数,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组织逻辑:知识密集型企业在初创期普遍盛行自由放任的文化和自组织机制。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它们又必须向“他组织”倾斜,拥抱制度与流程,强调控制的重要性,同时在企业文化上倡导群体英雄和集体协作精神。
然而,制度之度、管控之度、流程之桩界在哪里?自组织的边界在哪里?自组织如何与“他组织”有效融合?“他组织”如何让自组织有自由舒展的空间?群体英雄是否会抑制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凡此种种,无不显现着组织管理的悖论性与复杂性。
3
规则至上+群体英雄
导向的扩张形态与内耗机制的滋长
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走过原始积累期活力与无序并存的阶段后,为了使组织不致因规模扩张而崩溃,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告别有方向感(以客户为中心)的经验主义,逐渐建立一套有方向感(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以及科学的制度与流程,以确保组织中个体与群体行为的稳定性、可信性、可量化与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制度与流程也重新定义了每个组织成员的角色认知:个人英雄不再被推崇,合作与协同将成为组织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
华为管理方法论:思科,还是IBM
过去20多年(1997年至今),华为在运营商业务领域的巨大成功,从其组织形态讲,是集团军运作的成功,是群体合作与群体英雄的成功:“一场战役,谁离开都遗憾,谁离开仗都照样打,照样打胜仗。”我在访谈广东原邮电管理局的崔勋局长时,他评价:“我们跟华为做业务,不是认可某个人,我们认可的是华为品牌,认可华为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华为公司比较特别,换谁做主管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华为在1996年面临一个选择:以思科为师还是以IBM为师?任正非拍板:“思科的管理太灵活,我们中国人思想太灵动,我们还是要选择IBM。”这里有个小插曲,任正非一行出访美国,在思科参访时,不凑巧的是,恰逢思科当时的总裁钱伯斯出差,他留下了一瓶有个人签名的香槟酒赠予任正非。设想一下,假使钱伯斯当时没有出差,这位大名鼎鼎的IT英雄与未来大名鼎鼎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英雄任正非相聚于思科总部,英雄相惜,交流顺畅,任正非也许会选择以思科为师,那么,后面华为的历史、思科的历史都可能被重写。后面10年,钱伯斯与任正非有过多次会面,但已是竞争对手之间的思想碰撞。即便如此,两位企业领袖仍是互为对方的魅力所吸引。
历史不能假设,华为选择IBM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逻辑――一个传统经典的美国老牌科技制造企业,一个凝聚着20世纪美国经典管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流程的伟大公司,从侧翼助力,把华为带上了从传统“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转型的“不归道”,带入了全球化企业的行列。
然而,也正是伟大的IBM与华为的管理者们携手并肩,在10多年之后,使华为染上了“IBM病”――美式大企业病,在某些方面步入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所定义的“有组织的无序”:在某些部门和某些管理者那里,方向感趋于模糊,逐渐偏离“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流程依赖导致人的主动性与创造能力被抑制、被弱化;干部晋升机制奖励那些循规蹈矩的“流程派”,拥有“破框思维”的基层员工和中基层主管常常被逆淘汰,流程从“第一生产力”部分扭曲成“奴隶的鞭子”;过于严密和复杂的制度与流程系统,往往难以承受意外经营事件、非经营事件的冲击……
马克思有一段话讲得极其精辟,“原先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应该协助我们趋向目的的手段,转而变成了目的,抹消了我们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制度与流程是工具,变革是手段,但组织的诡异之处,经常是在组织进化的轮轨上,变革异化成了目的本身,为变革而变革,借变革之名阻滞变革。而本来服从、服务于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与流程体系也异化成了目的,异化成了阻碍生产力,妨碍人的自主精神、创新精神的“怪物”。“怪物不可避免地会攻击创造出它们的人”。
制度与流程一旦诞生,便具有了生命属性。
非完美性:确定一个流程,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冒出一堆问题;接着又确定一组流程,解决了一组问题,整个系统又可能出问题;接着又建立更系统化的流程。解决一个问题会带来很多次生问题。打补丁,打更多的补丁,任何制度与流程最后都变成了缝缝䃼补的“百衲衣”。
递归性:制度创造制度,流程创造流程。
异化性:流程烦琐化,制度目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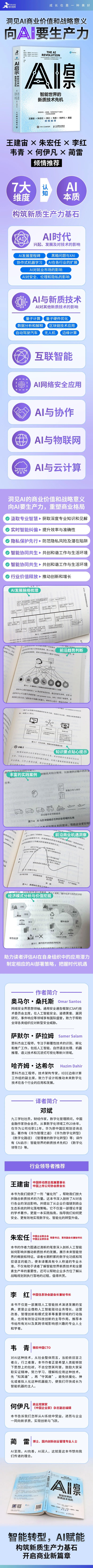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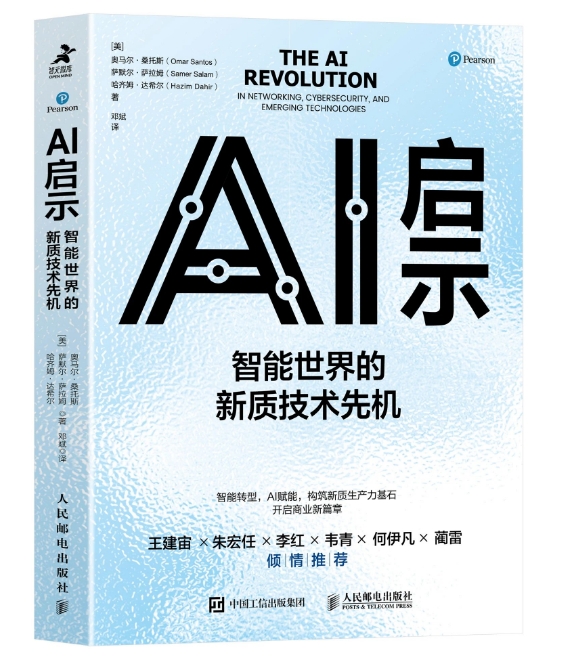
书享界保留所有权 |书享界 » 29年前,任正非为什么选择了IB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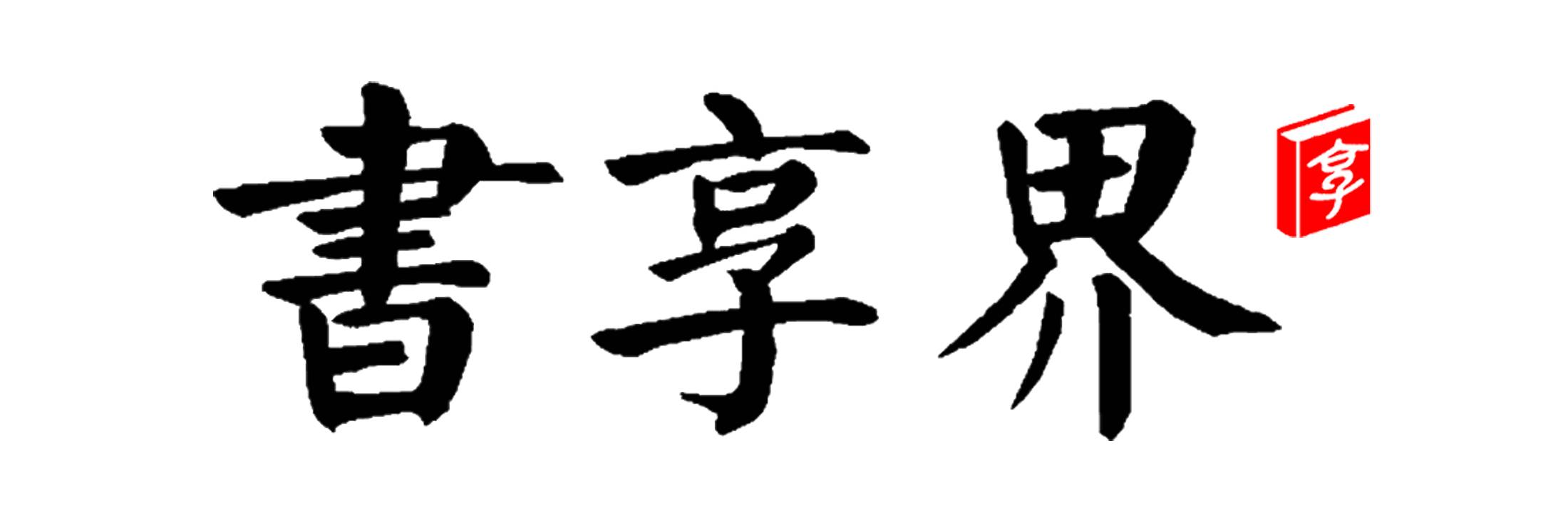 书享界
书享界